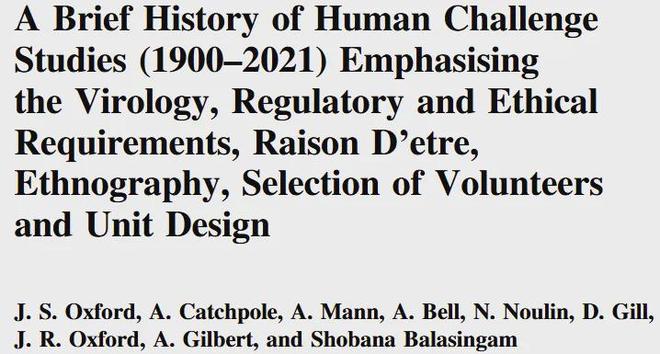明明知道存在可能被感染的情况,为何偏有人自愿去报名?这份知情同意书背后所蕴含的勇气以及信任,恰恰是人类挑战研究历经百年的核心命题。自黄热病发展至新冠,自简陋的小屋演变到负压隔离单元,这场围绕风险跟价值展开的博弈始终都未曾停止。
芬利与里德:蚊子实验背后的伦理分水岭
于1881年,古巴的医生卡洛斯·芬利作出了蚊子是黄热病传播媒介的猜测,他采用叮咬过病人的蚊子去叮咬志愿者,然而结果呈现出混乱局面,感染率未达到两成,并且整个过程缺少应有的规范,众多被实验者是那些缺乏相应地位、难以表达自身意愿的移民或者穷人,这一番操作所体现的更像是带有一定假设性质去进行冒险这种情形,而并非是那种严谨的科学验证行为。
在1900年的时候,美国军医沃尔特·里德接过了接力棒,他做了一件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事情,那就是要求每一位志愿者在参与之前签署书面文件,在这份文件里要明确告知实验目的、感染风险,并且承诺提供免费医疗和经济补偿。这份“知情同意书”在如今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了,然而放在120多年前那可是石破天惊的创举。虽然志愿者的构成,其中包括士兵和囚犯,依旧带有时代的烙印,但是它第一次把人放回了实验的主体位置。
冒险时代:科学冲动跑在伦理前面
在一战临近结束的时期,西班牙流感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。处于病原体都尚未得到确认的那个年代,法国科学家针对重症患者,把其支气管分泌物过滤之后,直接注射给健康的人 ;还有研究者把危重病人的血液进行混合并过滤,注射进自己身体内。这些实验所蕴含的风险几乎达到失控状态,隔离措施几乎不存在,更别提现代意义方面的伦理委员会。
这同一时期当中,日本以及美国同样开展了类似的研究,部分实验里的“志愿者”来源模糊不清,涉及到监狱人口或者福利院收容者,研究者并非完全没有善意,其一在于他们急切想要找到病原,其二在于拯救更多数目生命,然而却处于缺乏制度约束的状况下,科学冲动难以避免会越过边界,这个阶段的挑战研究,本质上属于公共卫生危机情境之下的应急赌博。
普通感冒单位:四十年的隔离实验场
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,《纽伦堡法典》得以公开问世,人体进行实验之时必须要遵循自愿、知晓情况、避免产生不必要痛苦这三大原则。1946年,英国的索尔兹伯里构建起了专门用以挑战研究的普通感冒单位。此地的硬件设施在现如今观看来是极为朴素的:志愿者居住于独立的小木屋之中,依靠打开窗户来实现通风换气,于乡间进行散步的时候需要与他人维持30米的间距。
条件较为简陋,然而规则极其严格。这里的工作人员历经良久的训练,其操作流程近乎刻板,毫无灵活性可言。就是这样一个带有“复古”色彩的单位,运行了长达四十多年之久,首次成功分离出人类冠状病毒,进而证明了普通感冒与冠状病毒之间存在着关联。它清晰地表明:严格的规程以及经验丰富的团队,在某些时候比那些价格昂贵的设备更能够守住安全底线,守护住至关重要的安全防线标点符号。
商业单元与负压:隔离技术如何驯服风险
今天进行的商业挑战单元之中,像位于伦敦的hVIVO,已然运用了负压隔离舱以及HEPA高效过滤系统。空气呈现只进不出的状态,病毒颗粒被阻拦在滤网的内部,污水也是经过高温灭活之后才予以排放。志愿者的鼻腔冲洗、血液采样都是在隔离间里完成的,研究人员进出的时候需要穿着全套的防护服。
存在这样一种设计,其目的并非进行科幻感方面的营造构建之举,其目的在于同时对三件事情予以保护呵护,这三件事分别是,保护维系志愿者不遭受外界的污染侵害,保护外界不受到病毒泄漏所带来的威胁危害影响,保护研究数据不受到交叉感染所产生的干扰妨碍侵扰。在新冠疫情期间这段时期之内,这么一套系统曾经被迅速快捷地调用启用,进而成为全球范围内首批获得批准认可的新冠病毒挑战研究平台。在技术实现升级提升的背后背后之处,是社会对于风险容忍度的收窄缩减,也是对于志愿者生命权更为具体详细的尊重敬重敬畏。
小规模大价值:为什么还要主动让人感染
有一种疑问有可能会产生,那就是:自然感染同样能够收集数据,为何还要去冒这样的风险呀?其中的关键区别之处在于精度这一方面。有着这样一种挑战研究,能够精确地知晓感染的时间点,以及病毒剂量,还有毒株序列,借助这些可以将从感染直至康复的这个过程,拆解成为缓慢播放的镜头,一帧一帧地去分析免疫系统的变化情况。然而这种精细程度呢,乃是社区试验没有办法做得到的。
从成本方面来看,传统疫苗的III期试验,需要去招募数万人,还得等待流行病季节,这一过程会耗时数年,并且要耗资数亿美元。而挑战研究呢,仅仅只需几十到上百名志愿者,在几周的时间内,就能判断出疫苗是不是能够有效地阻断感染,或者至少能够减轻症状。在历史上,对于伤寒结合疫苗以及口服霍乱疫苗的获批,挑战研究所提供的效力数据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它并非是替代大型试验,而是帮助大型试验去排除那些无效的选项,从而把资源留给更具希望的候选者。
当下铁律与未来边界
1999年,美国有一项流感挑战研究,因出现一例志愿者呈现严重呼吸衰竭状况,从而全面暂停,相关研究陷入停滞状态近十年。这起事件致使整个领域认识到,就算概率极其低,也绝对不可以用任何人的生命去进行赌博。所以,如今的挑战研究门槛非常高。
志愿者年龄限定在18至55岁之间,要经过心电图、胸片、血液生化等几十项筛查,以此确保心肺功能健全,并且对挑战毒株不存在抗体。知情同意书得逐条进行讲解,还要留出至少24小时的考虑时间。研究需要经过独立伦理委员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的双重审批,隔离单元必须紧邻具备救治能力的大型医院急诊科。最近的新冠挑战研究,是在WHO全球伦理框架指导下,克服了毒株生产、监管审批、公众沟通等多重新难题。
回溯过去的一百多年,出现过芬利那模糊不清的叮咬情况,还存在里德那份有些泛黄的知情同意书,直至如今负压舱内精准的采样行为,人类挑战研究的整个进化历程,实际上是对人的尊严理解程度逐步加深的过程。那些在知晓相关情况后依旧进入隔离区域的志愿者,跟背后的研究者相同,都是公共卫生防御战里默默无语的建设者。这项研究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,然而它的存在本身就在回应一个问题:当科学有对人体的需求时,社会应该用什么去进行交换?
设若此刻存在一项关联新冠的挑战研究,此研究要求健康的志愿者去感染已知的变种从而对新疫苗展开测试,那么你觉得参与其中的人员应当获取怎样的补偿呢——是金钱补偿,还是荣誉补偿,又或者仅仅是单纯的公益贡献呢?欢迎于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